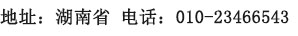白色的情人,黑色的妈妈
色彩宛如琴键,眼睛好比音锤
心灵有如绷着许多根弦的钢琴
艺术家是弹钢琴的手
只要接触一个个琴键,就会引起心灵的颤动
——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肖邦《夜曲2号:降E大调》惠斯勒《肉色与绿色的变奏曲》,年年5月的一个清晨,八点已过,雾都伦敦的春天,难得一见的太阳挂在了泰晤士河上,温暖的春光洒进伦敦西区一间临河公寓的别致客厅里:在柔软的波斯地毯上,花盆里粉色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大理石的壁炉上,一枝同样粉色的茶花倚在青花瓷瓶之上——这是来自美国的艺术家惠斯勒的伦敦公寓。这位走到哪里都不合时宜的画家此时早已醒来,他头发蓬乱地坐在钢琴边,若有所思地在黑白琴键上摸索着几个奇怪的和弦,为他即将开始的作画寻找灵感。说起音乐,他最喜欢的钢琴家就是肖邦。他为什么要在作画前弹钢琴,对此,他曾解释说:自然包含绘画了所有的颜色和形式,就如同钢琴键盘包含了音乐所有的音符。艺术家天生的工作就是,在其中挑选组合那些最美好的元素——音乐家收集他们的音符,直到构成音乐独特的和弦,画家摆弄他们的模特,倾听自然的声音,直到从混乱的光影中找到和谐为止。所以每次作画前,为何不能在钢琴边寻找灵感?惠斯勒的这些高论,很多年后曾在法国巴黎的艺术沙龙里宣讲,只不过他的法国同行们总觉得这家伙脑子有问题,现实主义画派觉得他的画不够写实厚重,印象派又觉得他的画太抽象。回到伦敦的家,他那些热衷于画唯美仙女的英国同行们又觉得他的画太没文化内涵,太东方。19世纪末,巴黎是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主义画派崛起的时代,惠斯勒的绘画,以及他关于音乐与绘画的高论,在绘画圈里一直吃不开,倒是引发了法国前卫音乐家德彪西的强烈共鸣——惠斯勒要在画布上作曲,德彪西要在五线谱上作画。老照片:惠斯勒,不合时宜是惠斯勒的标志,对此,他早就不以为然。他是美国人,一生却在巴黎与伦敦摇摆,可是混了那么长时间,法国人、英国人还是把他看作异类。他如他喜爱的钢琴家肖邦一样,年少离家,叶落也没有归根,不同的是:一个不愿意,一个是回不去。他在法国学画,和印象派大师莫奈、德加是同学。德加曾说,如果这家伙要不是画画,一定是个大恶棍。惠斯勒喜欢别人把他当成恶棍,当成异类,在艺术的世界里,他已经走到了地图的边缘,在世界的尽头,他独自沉醉在属于他和她的仙境里,倾听着流动在光影中的神秘旋律——他早已不在乎这个现实世界的喧嚣。五月花似梦,他一边抚摸着黑与白的琴键,一边看着他的女人乔安娜·希芙兰(JoannaHiffernan),慵懒地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他亲热叫她乔(Jo)。此时乔已经穿好了惠斯勒特意为她准备的细白麻纱质长裙,戴上了珍珠耳坠,手中拨弄着惠斯勒不知从哪里淘来的东方式圆扇,蓬松的红发拢在肩后——虽然画好了妆,但她神情依然象刚刚睡醒的公主。惠斯勒并没有给她规定任何姿式,他只是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公主,安静下来。德彪西:缓慢的圆舞曲惠斯勒《白色交响曲2号:小白衣女孩》模特:乔安娜·希芙兰早晨八点后的阳光,温暖如絮,窗外已经苏醒的街市和泰吾士河上隐约传来混沌的嘈杂声。配合着惠斯勒胡乱按下的钢琴和弦,就仿佛一支古老而神秘的音乐——然而我们的惠斯勒,并不是玩音乐的,他是坐在钢琴边的男巫,正在寻找音与色奇异的通感,寻找传说中神秘花园的入口。惠斯勒犹如一个固执的顽童,在琴键上耐心地寻找着、或者更准确地说,等待着他心中“和谐的声音”的到来——乔安娜终于停止拨弄手中的扇子,她来到壁炉边,早晨的阳光透过左侧白麻平纹布的窗帘,柔和均匀地洒落在美人雪白的衣裙上,照亮了她雪白而泛着金色的肌肤。乔,回头看了一眼她那桀骜不驯的男人,什么也没说。然后,她单手倚着壁炉,扭头默默注视着壁炉上那支从中国花瓶伸出的茶花,一侧耳畔的珍珠耳坠在晨光中闪烁着优雅而迷人的光芒,然而壁炉后的镜子却映出了一抹隐藏着的忧伤.....就在这一刻,她听到惠斯勒从钢琴边站起来,快速来到正对着她的画架边,开始创作他的——《白色交响曲,第2号:小白衣女孩》。屋里安静得可以清晰地听到俩人炽热的心跳,尘埃沿着越来越明亮的光线莫名地飞舞着、坠落着——这是属于他和她的时间,在安静而美丽的时光深处安放着的其实是两颗不平静的心灵:分手在即,他们谁也不知道,命运将如何谱写这段爱情的乐章。相爱的人拥有的唯有此刻,琴瑟相交,花开正好——这是属于他们的交响,两颗心在共鸣中,流动着只有他们才能听到的、爱的旋律。惠斯勒《白色交响曲1号:白衣女孩》这是一幅充满了色、香、味的音乐名画。它可能不同于你对宏大交响曲的印象,或者改成“白色奏鸣曲”会更贴切一些,其实对惠斯勒而言,“交响”大约指是光影、人物,心情的流动与交织。
说来有趣的是,两年前,他以乔安娜为模特创作的《白色交响曲1号》,副标题是“白衣女孩”,那幅画轰动了年巴黎的“落选沙龙”,无辜的白衣少女站在凶猛的狼皮垫上,让当时的法国人、英国人惊吓不小——它那随意的风格、笔触,不符合那时肖像画的传统。两年后,惠斯勒沿用了旧标题,但却在原来的副标题上加了一个“小”,仿佛两年的时光,他的“乔”不仅没有变老,还小了两岁。
爱是一种很奇特的存在,它总是固执地、自不量力地要和现实与时间作对。所有的甜蜜和忧伤,此刻,正肆无忌惮地充满了惠斯勒画室,甚至让他忘记了——执意要拆散他们的母亲大人,即将到来。惠斯勒画得很快,快到中午时就已经画好了作品的框架和人物的造型,他只需要再打磨一下细节。他从来不像其它当时英国的画家们那样,要费事地折腾模特很久很久,直到把一个姿式摆成了僵硬的树桩。惠斯勒很少象他认识的那些英国拉菲尔前派画家那样,总是刻意地把画中的每一个细节,打磨得如同真的一样。他只是乘着热情还没有熄灭时,快速地画出初稿,然后,他会让模特走开,自己一个人对着画布完成剩下的全部细节——他不喜欢长时间地面对真人,也讨厌去描绘真实的细节,他认为那是摄影家的事。惠斯勒《紫藤与玫瑰,以及六件中国瓷器》模特:乔安娜·希芙兰给惠斯勒作模特是轻松的,他甚至不喜欢给模特规定姿式。相比之下,做惠斯勒的情人大约要艰难许多。因为乔安娜明白,这个放荡不羁的男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妈妈宝贝”。这不——下个月惠斯勒的老母亲,就要从美国赶来看望儿子。在母亲大人到来之前,经济上完全依赖母亲的惠斯勒就在信中保证:会和同居了四年的乔安娜分手。在妈妈和爱人之间,乔安娜没有任何胜算。她必须在母亲大人到来前搬走、消失。因为在惠斯勒的母亲心目中,“女模特”是“表子”的同义词,更何况她还是一个从爱尔兰乡下来的野姑娘。她当然舍不得与惠斯勒在一起的、整整4年的光阴,形影不离——她是他的缪斯女神、他的火焰乔,他的小白衣女孩。乔安娜的父亲、姐姐甚至亲切地叫惠斯勒——我的女婿,我的妹夫。惠斯勒的朋友也很喜欢这位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人。一位朋友后来甚至对惠斯勒说:你一辈子,也不可能把她的颜色从你的画布上抹去。如果这忘不掉的,却又无法留住,甜美的回忆在命运面前,到底又有何用?!惠斯勒也许并没有那么多伤感,此刻春光正好,他已沉醉不知归路。然而在乔安娜的心中,却已是一片“无计留春住”的惆怅。惠斯勒《一位艺术家的母亲》德彪西《沉思曲》年5月,惠斯勒起初想的大约不是分手,因为母亲不会留在伦敦,也不会跟他去巴黎。就算她不辞辛苦地、不断地跨海来“视察”,也很容易对付。只不过,这一回有点不一样,他的家乡美国正在打内战,母亲在伦敦一呆就是几年。再加上一起逃过来的还有惠斯勒烦人的阿姨,她们时刻监督着,惠斯勒是否还在和旧情人暗送秋波。当母亲大人驾到,乔,只能乖乖地搬走了,带着惠斯勒的安慰与承诺。眼下,一向放荡不羁的美国画家,只能在妈妈和阿姨面前装老实。他甚至连新的模特也不敢请。为了画画,惠斯勒只能请母亲大人为他做模特,他原本想让62岁的母亲和乔一样,站在壁炉边,但是母亲站不住,于是儿子只能妥协,老老实实地画了一幅著名的母亲坐像——《黑与灰的协奏曲:一位艺术家的母亲》。也就是英国电影里,被憨豆先生恶搞的那幅——很贵、很贵的名画。和乔安娜的白色相反,画中的母亲是黑色的,窗帘也是黑色的,所有的光芒都消失在全黑的衣裙与灰暗的墙中。春日明媚的阳光,也换成了母亲坚定的目光,冷漠地掠过黑色窗帘上白色的碎花,空洞地停留远方——那是美国,惠斯勒发誓一辈子也不回去的家。当时这幅画展出时,英国艺术评论家一片哗然,一个人怎么可以把母亲画得如此冷漠无情,按照当时英国艺术流行的矫揉造作的品味——母亲肖像就应该闪烁着圣母的慈爱光环。奇怪的是,当你把这幅杰作和他为乔安娜画的《白色交响曲》系列放在一起时却有一种莫名的和谐。站与坐,真花与假花,温情与冷漠,青春与衰老,构成了我们生命之旅永恒的主题。更奇怪的是,当你久久的凝视这幅“冷陌的肖像”,你看到的并不是死寂与丑陋,你依然可以从黑色窗帘上流动的白色碎花,以及轻轻飘浮在全黑长裙上的透明白色蕾丝中听到某种音乐的微妙协奏——这是一位衰老的女人,但惠斯勒画出的却是她逝去的美丽、浪漫与温柔。这是一位艺术家的母亲,无论是乔还是母亲,对他而言都是一份来自女人的爱,它可以炽热如乔火红的长发,也可以沉静如母亲黑衣上淡淡的蕾丝花边——这是黑与白的协奏,而不是有关爱的艰难选择。至少,对惠斯勒而言,这两份爱似乎并不矛盾。她隐没在梦中
你隐没在梦中
宛如雪化在火中——阿尔蒂尔·兰波《奥菲莉亚》
肖邦《E小调夜曲》OP.72惠斯勒《夜曲:寂寞》母亲是一棵树,根永远扎在家里。儿子是一只鸟,心儿总是飞向远方。惠斯勒当然知道,无论母亲如何生气她都会离开,回到美国的家中,等待永远不归的儿子。到时候,他又可以和他的“火焰一样的乔”一起继续燃烧。被英国、美国美术界一致排挤的年轻画家,除了对艺术狂热的理想,他更需要母亲为他提供的年薪。他的确喜欢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也爱着乡下姑娘“乔”那无法言喻的热情与忧伤。然而母亲和阿姨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摆平的。结果,暂时的分手,成了天各一方。对此,乔安娜早有预感。乔安娜知道,情人母亲从美国跨海而来,事情就一定没那么简单,女人与女人之间可以有和解,但很少有接纳,特别是婆婆和儿子的情人之间,即使她已经为了她的男人怀上了孩子,也无济于事。只要那个黑衣的女人不同意,只要她的男人一天不经济独立,只要惠斯勒拒绝选择,她们再美的爱情也终究是镜花水月。惠斯勒母亲已经容忍了儿子不好好读书,跑到法国、英国画画。要知道,按照她的原本规划,儿子应该读完西点军校,成为老惠斯勒那样名满世界的伟大工程师或者军人。只可惜事与愿违,儿子因为“举止轻浮和化学不及格”被以严格著称的西点军校开除。他只想画画——这又有什么办法,母亲最后妥协了,但她依旧担心,漂洋过海的儿子,会被伦敦和巴黎满大街妖媚又堕落的女人们带坏。她也不放心惠斯勒在伦敦的姐姐——那是他花心父亲的私生女,另一个因堕落而生的女人。库尔贝《睡美人》年,惠斯勒的母亲带着阿姨到达伦敦时,乔安娜只能搬走。但承诺中的复合却迟迟不能到来。年,在母亲和情人的双重夹击下,惠斯勒干脆一个人逃走了,他把自己那些没人买的画作和收集的东方瓷器,扔给乔安娜代售,自己跑到南美溜达了一圈,远离两个他最爱的女人。乔安娜知道:一旦离开,她那有着野马一般心灵的男人,就会去寻找新的交响,新的公主,新的女人。她已经无法主导这场爱情。可是乔安娜,又怎能就这么认输?她要用自己最原始的方式,提醒着他的男人——美的花蕾一旦绽放,她就不再是树下的一棵野草,不再是乡下的一朵野花;盛开的百合,你不去及时摘取,总会有人寻香而至——到时,你会追悔莫及吗?年,眼见着无法兑现复合的承诺,也眼见着无法安置昔日的恋人,惠斯勒干脆把乔安娜介绍给了他的法国老哥们、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结果奔放的库尔贝毫不客气地把惠斯勒的女神画进了自己的画中。年,库尔贝画了著名的情色画《睡美人》,画面中有两个相互交缠的女人,核心却只有乔安娜一人,她微闭着双眼,散乱着秀发,潮红的两颊,沉醉在情欲异色的风暴中。更要名的是人们都在猜测库尔贝那张惊世骇俗的粗野名画——《世界起源》中的女人也是乔安娜,整个巴黎都在八卦——乔安娜已经是库尔贝大叔的新任缪斯。惠斯勒这下慌了。年,他急忙从南美写信给乔安娜,责问她是否变心。德彪西《贝加摩组曲:月光》惠斯勒《夜曲:切尔西》深秋,从遥远的南美归来,惠斯勒眺望着浓雾弥漫的泰晤士河口,严重的工业污染和伦敦深秋的冷雾,让整个世界变得朦胧而混浊——你看不到月亮,但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冰冷的手指拨动着你寂寞的心弦。那火一般的爱情真的熄灭了吗?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他的“乔”,是否仍在浓雾的深处等待他回家。许多事,其实还是不知道最好,知道了,难免耿耿于怀。年深秋,爱情是一朵永不再开的花。乔,回家了。但问题是,她的心再也无法和他的男人象往昔一样和谐共鸣。她仍然无法和惠斯勒生活在一起,甚至不能在自己家见他,她只能和惠斯勒相约在朋友的画室。对她而言,他的惠斯勒回家了,但他的承诺却留在了远方——这是一个永远不愿意作出选择的男人。你又怎能在妈妈与情人之间选择呢?这是一对撕裂了惠斯勒心灵的不协和音。这种撕裂,破坏了惠斯勒心中原本的美梦,却又在裂缝处,为我们创作了一个新艺术世界。肖邦《升F小调夜曲》OP.48惠斯勒《夜曲:老巴特西桥》年,惠斯勒的画风突变,从描绘光影中的美女转向描绘内心暗淡的风景。在旅行途中,他完成了三张灰暗朦胧的风景画。这三张充满了神秘音调的画作,令当时欣赏惯了写实风景的英国人万分捉急,也让迷恋明亮光影的法国人胸闷,惠斯勒以肖邦的《夜曲》命名了他的新作。在古典音乐中,“夜曲”(nocturne)是一种很私人化的钢琴曲式,忧郁,深沉,同时具有很强的歌唱性。英国的费尔德和波兰的肖邦创作了大量深情而优美、饱含诗意、纠结着爱恨、缠绵于回忆与现实、如梦似幻的夜曲,它们有着一种特有的安静而寂寞、惶惑而迷人丽。肖邦写了一辈子的《夜曲》,惠斯勒《夜曲》以三张画开头也延续画了十余年,画家创作的重点从人物转移到了景物,他的画笔不再诉诸于外在的光影与形状,更多求之于内在的感受。景与物皆若隐若现于散不开的冷雾中,模糊了时间、地理、人物,然而有一种神奇的音调和情绪,却出没于那流动而微妙的暗色之中。惠斯勒《白色交响曲3号》乔安娜在画面左边惠斯勒的乔,回到了她深爱有男人身边,默默地接受了现实的一切。他们没有争吵,但是那段脆弱而美丽的爱情早已凋零,就如同年春天娇嫩的粉色杜鹃花。惠斯勒唯一兑现的承诺是完成了《白色交响曲3号》,这是惠斯勒人物画最后的杰作。乔安娜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了惠斯勒画中。然而昔日的公主乔已经被新的女孩挤到了画面一角,仿佛一朵凋零的百合。那象征着两人相爱的东方团扇,也从美人指间失落在了人间。或许它原本就是一个梦,一个从来不曾醒来的梦?或许他们原本就一对从来不曾解决过的和弦?一段失落在梦境中的旋律?《白色交响曲3号》也成了两人爱情最后的绝响。爱情模糊的调性,最后回归在一段迷一般的春色中。春梦了无痕。在灰暗的背景上
你是一支遗忘的歌
请把这一滴像猫眼石碎片一样闪着幽光的苍白眼泪,收进掌中再放进远离太阳的,他的心里——波德莱尔《月亮的哀愁》德彪西《夜曲之三:女妖》钢琴版
年之后,乔安娜隐没在惠斯勒的生活中。但她始终没有离开。她就宛如在灰暗的背景上,一支遗忘的歌。而惠斯勒绘画的重心则完全转移到了风景画中,他画了整整十年的《夜曲》,仿佛年春天的阳光,再也没能穿透他心中浓得化不开的冷雾。这冷雾弥漫不散,直至吞没了物象的边缘,心灵的边界。奇怪的,惠斯勒不仅极少创作大型的人物画,而且,他也不再热衷于把他收集的东方的器物、服饰、小玩意,放进他的画中。要知道19世纪未是东方艺术深刻影响西方绘画的时代。相比法国印象派画家,热衷于描绘身着东方服饰的西方美女,惠斯勒已经走得更远,他不再满足于用西方的光影笔触去描绘东方的服饰与器物,那些令人惊异的《夜曲》,本身就浸透了一种日本浮世绘式的构图和中国写意山水画中流动的神韵——简洁,内省而抽象。中国山水画中有一句名言:看山画山不是山。热衷风景画的惠斯勒也从来不对着风景写生,他对朋友描述自己创作《夜曲》的过程——深夜一个人出去溜达,象幽灵一样地盯着沦陷在烟雾与污染中英国现代都市:那些藏在夜色里的灯火,就象幽灵。那些桥,那些建筑,那些工厂,都失去了原本巨大的声音与形状,它们就象倒映在梦中的山峰,童话中的宫殿.....不同是,所有的景物都仿佛在沿着夜色在流动、消失.......但他只是看,不会画。凌晨,他会回到家中,好好睡一觉。醒来后,他才会凭着模糊的记忆,画下看过的风景。只有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你的心灵才能和这个世界荒凉的心灵发生共鸣,你要画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和世界的共鸣,就象一对和弦。惠斯勒《黑色与金色的夜曲:坠落的烟火》
这些奇怪的画作,在他生活时代,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它难以解读的抽象,甚至引发了艺术圈的震动。年,他的画作《黑色与金色的夜曲:烟火》在英国格洛斯威侬画展上的展出,凌乱的笔触和难以解读的细节,是对大众审美的一次挑战。当时,英国最有权威性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正好看到了这幅画,第二天他就著文大骂惠斯勒的绘画是胡闹,他在报纸上评论道:把一桶颜料直接泼到观众脸上,还要向人索要二百几尼的金币,这不是欺骗,这是抢钱!惠斯勒的脾气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何况罗斯金此言一出,向惠斯勒订画的客户也大大减少了。于是,惠斯勒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官司打得很热闹,它涉及的是艺术这种无法捉摸的事,原告和被告又都是艺术界的风云人物,如何判决是对法官的考验。在法庭上发生了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辩论:律师(拉斯金代理):《黑色和金色的夜曲:坠落的烟火》主题是什么?惠斯勒:这是一幅夜景,表现夜里克里蒙花园的焰火律师:不是克里蒙花园的景色吗?惠斯勒:如果真是花园景色,恐怕观众就失望了。这是艺术创作我将它称之为夜曲……律师:这幅画你画了多久?惠斯勒:可能几天吧,一天动笔,另一天完成律师:就两天工作,你(居然)要价几尼(老金币)?惠斯勒:不,画的价格包含了我用一生获得的知识德彪西《夜曲之二:节日》钢琴版德彪西和中国花瓶最后,法庭裁决惠斯勒胜诉,但指出:这场诉讼无事生非,纯粹是艺术圈子里的纷争。惠斯勒只得到了象征性的四分之一便士的赔偿,但他却为这场官司却支付了大笔的诉讼费,使他于年5月不得不申请破产。惠斯勒的住宅、收藏和大量作品被迫廉价拍卖。这对本来就卖不出画的惠斯勒打击重大。这场官司弄得两败俱伤,罗斯金输了道义,动摇了权威;惠斯勒则输掉了钱财。惠斯勒于年发表了小册子《惠斯勒对罗斯金——艺术家对艺术评论家》。文中惠斯勒阐述了自己的新艺术观,这倒使他名声大振。赢得了年轻艺术家们的一片喝彩。小册子不断再版,并成为后来点拨德彪西创作新音乐的契机——既然惠斯勒可以用色彩光影来表现音乐的律动,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音乐来描绘我心中的梦境呢?受惠斯勒《黑色与金色的夜曲》的启发,德彪西创作了著名的音画——《夜曲》,对此德彪西解释说,他的《夜曲》和肖邦不同,不是音乐的体裁:夜曲的标题,在这里应作较一般性,尤其是较富装饰意味的解释。它不采用夜曲惯有的形态,而以特殊的印象与光影为焦点,烘托出所包括的所有意象声声相和,构成了音乐的色彩;声声相继,就有了流动的旋律。音乐和绘画一样,都是探索心灵的道路。音乐不仅仅是写给耳朵的,就象绘画不仅仅是画给眼睛的。年德彪西,穿越了迷惘的青春,经历惨痛的爱情,当他从远方流浪归来,站在巴黎夜色中的阳台上,望着节日中盛大的烟花,一定百感交集。年,当永失我爱的惠斯勒仰望着巴黎克里蒙花园的焰火,在漆黑的夜空中绽放,然后飘落无声,那些无法忘记的爱早已再难追寻,火光中,他是否曾片刻地想起过她?他的爱人已经坠落在黑夜深处,她比烟花寂寞!尾声:你还记得我吗
她以绝美之姿而来犹如夜色
——拜伦《美之诗》
惠斯勒年轻时的标准像消失的乔安娜不懂得这么多深奥和艺术哲学。没有结局的爱情,就象没有结果的花,早已飘落成泥——当她无法成为他的爱人,她只能珍藏着自己的回忆,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回忆里有她失望的爱情,更因为那段回忆里藏着她一生最美丽的一段生命,一段流动在五月春色中的白色旋律,一段闪现在夜空中的灿烂烟花。乔安娜最后一次出现在惠斯勒的视线中是年,那年惠斯勒和一位美国来的富商之妻——雅培夫人去威尼斯旅行时,曾给伦敦的私生子(很可能就是他与乔安娜的孩子)写过一封信,在信的最后,他写了一句——代我向乔阿姨致意!然而,这也就是可怜的女人得到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