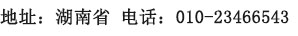书籍《夜航西飞》曾描绘过一个孤独星球般异常静谧、柔美的非洲大陆,作者驾驶飞机,暗夜里穿行而过,机身阴影下是或驻足栖息、或结队移动的象群。我将这样的意向说与吴辰,想知道他看过、经历过的非洲生活是否如书籍中描绘的那样,有着神秘的孤寂。
单位节日准备。
电话那头的吴辰隔着时差,缓缓讲述着他长达8年多的莫桑比克生活。这里属热带草原气候,常年温润,公里长的海岸线包裹着这个沿海国家,以富饶的海洋资源喂养着人们。由西北至东南的地形地势,形成高原、山地、平原等不同梯度的地貌景致。
吴辰的工程项目建在首都马普托,相较于其他地区,马普托的样貌有着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的影子,不富裕,但人们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努力。吴辰和当地数万华人华侨一起,经历着不同文化、肤色、人种的异域风情,用做工程、搞贸易、建农场的实实在在的劳动,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以下是他的自述。
项目组照片。
我是一名国企员工,年11月份来的莫桑比克,完整的计算已经8年三个月了,每个春节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当前从事的工作是工程建设领域和新业态的基础设施开发工作。之前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参与马普托环城路项目的具体施工,项目历经三年多完工,现在做具体的市场开发工作。
莫桑比克城市的部分面貌,包含我们施工的桥梁。该桥梁完工时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亲自到访过。
回看过去这些年,我自己总结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环境尤其是国外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鲜期,第二阶段是烦躁期,第三阶段是平静期。
来之前企业帮我们准备了大量资料,我自己也有在网上查这个国家的情况。了解后更多是新鲜的心态,不会有太多忐忑或担忧。一出机场,映入眼前的是周围低矮错落的建筑,有点像城中村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高楼,这个地方确实有点穷,经济水平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
但当时更多的还是被异域风情所吸引,好奇每间屋子,它们的主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如何与当地人交流?我的工作要怎么开展?会接触到哪些人呢?一个个从没接触的问题充满着脑海。
真正安顿下来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是水土不服,老容易上火。来的时候国内接近冬天,这里却很热,温度也不是很适应,还要倒时差。我们来了一支9人项目组,还包括一名中国厨师,饮食问题算是解决了。能够吃上了中国饭菜,那个地方就不陌生了。
马普托是莫桑比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昨天我还估算了一下,这里有近五万多华人华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开餐馆的、有做中国援助项目的,这里的中国农场就是湖北省的对口援助项目。
莫桑比克夜景。
生活方面还好说,工作方面确实碰到一些问题和难题,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栽过跟头、交过学费,但也有不少积累的经验。施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本地人讲葡萄牙语,我们彼此交流主要讲英语,英语学了那么多年,真正用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二个问题是不理解当地人的一些做事习惯,当时有一个本地人,也是熟了以后,就问我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喜欢找捷径。其实我理解的是我们时间观念强、做事讲求效率,但他们就总觉得不按既定的规定来,更多是看中目标而不是过程。
我个人还有一个感受是,当地人还是能分得清楚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也不会因为关系好就改变原则。国内可能会有一些人情会主导一些东西,间接影响一些决策,但在这里更多是规则、法制、组织起主导作用。
马普托环城路项目施工过程中。
我们的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有一个本地的项目总监,是位津巴布韦老头,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刚开始接触时觉得他对我是百般刁难,现在想想更多的是帮助吧,帮助我迅速适应角色和环境。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们的争议聚焦于桩基水泥混凝土塌落度的问题,这是混凝土的一个重要质量检测指标,我们在国内的规范规定是-mm之间就是合格的,但是老头坚持不愿意,拿着规定较为宽泛的南部非洲规范SATCC,一定要把数值范围控制在并没有针对桩基这一项要求的30-mm内。这其实是因为彼此不了解而产生的信任问题,我们也是在尊重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
津巴布韦老人的照片。
但是当地人也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我有一次坐车出差,正走着迎面一辆车突然对我们闪了几下灯,我好奇的问司机闪灯原因,本地司机解释,那是在提醒我前面有查超速的,让我们注意行车速度。由于本地的测速是人工站点,它随时移动,你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
跟本地人打交道多了,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他们。最早我们接触的普通工人,做的基础工作,收入低,消费主义的观念又很盛行,真的是有多少花多少,一拿到工资就去酒吧了,从来不考虑存钱,也很少给家里老婆孩子生活费。后来聊的多了也慢慢理解了他们的生活观念,因为贫穷,这里的人平均寿命也不高,人生的